格特鲁德·斯泰因是一位富家女子。她曾经在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过论文。后来,她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医学院的前两年,她研究的是胎儿的大脑。斯泰因小姐聪明勤奋,她学会了切除脑皮层、在福尔马林溶液里保存组织细胞。学习之余,她喜欢拳击和抽雪茄。老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
然而,斯泰因小姐慢慢地对临床医学失去了兴趣。她不再学习有机化学,也不去背解剖课的笔记,而是熬夜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斯泰因小姐走火入魔了。她的医学笔记写得晦涩古怪、不知所云。一位教授看了她的笔记之后说:“不是我疯了,就是斯泰因小姐疯了。”
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批像斯泰因小姐一样的疯狂的现代艺术家。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里尝试写一种无韵的诗歌。他的诗越写越叛经离道。在《草叶集》第二版中,惠特曼坚持收入类似《我就是那个渴望性爱的人》( I Am He that Aches with Love)、《处女膜啊!有处女膜的人啊!》(O Heymen! O Hymenee!)等让正人君子们痛心蹙首的“下流作品”。
1910年,塞尚的画作第一次公开展出。当时的报纸评价说,塞尚先生的作品“除了可以为病理学学生和研究变态课题的专家提供素材之外,别无他用”。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刻意地惹恼他的听众。当他的《春之祭》第一次公演的时候,观众一片哗然,保守的听众和新潮的听众当场厮斗。还没有演完,剧场的人就都走光了。
1903年,斯泰因小姐到了巴黎。她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群新锐的艺术家团结在她的身边:马蒂斯、布拉克、格里斯,还有神秘多变的毕加索。毕加索曾经给斯泰因小姐画过一幅肖像。看过的人都说画得根本不像。毕加索说:“将来会像的”。那个时代的先锋艺术家们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傲慢和自负,他们知道,自己和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
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科学和理性至上。
所谓的科学,乃是像物理学一样严格清晰的学问。人世间的一切必须都找到精准的规律。拉普拉斯是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他曾经当过拿破仑的内政部长。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在他五卷本的关于宇宙规律的著作里没有提到上帝,拉普拉斯说:“我不需要那种特定的假设。”拉普拉斯认为他的科学理论能够解释一切社会规律,他把自己创造的这个新学科称为“社会物理学”。正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说,当时的科学家热衷于对社会做“活体解剖”。
但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拒绝对冷冰冰的科学屈服,他们开始了艰难而寂寞的探索,他们转向对自己的内省,沉醉于对人类心理奥秘的深层体验。马塞尔.普鲁斯特整天躺在床上,任由自己的思绪飘荡。塞尚会持续几个小时盯住苹果看。他自负地说:“给我一个苹果,我就能震惊整个巴黎。”连小孩子都能听出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曲子充满了不和谐音,但他坚信噪音也是音乐。斯泰因小姐兴致勃勃地玩弄文字游戏,她的餐盘上印着自己的作品:“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多年之后,科学家们才发现,这些疯子一般的现代艺术家们远远走在脑神经科学的前面。他们是一群先知,在朦胧的摸索中,他们已经接触到了意识的本质。
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尔认为,灵魂和身体是分离的。我思故我在,身体不过是一具皮囊。惠特曼则告诉我们,灵肉是无法分开的。他在新奥尔良看到奴隶交易,让他深受刺激:落在身体上的鞭笞,同样也把心灵抽得血肉模糊。他在弗吉尼亚州的部队医院里做志愿者,照顾伤兵,每天目睹手术台上四溅的血滴、耳闻伤员们的惨叫,眼睁睁地看着无人认领的尸体腐烂发臭。惠特曼敏锐地注意到,很多士兵失去了肢体之后,会出现一种幻觉,仿佛自己的肢体还在。即使肉体已灭,意识仍然拘牵。
科学家后来做过一个试验:一群牌手摸牌赌博,若依理智,大约摸80轮牌之后能找出赢牌的规律,但要是顺应感觉,大约摸10轮牌,当拿到好牌的时候,手就会格外紧张。科学家在受验者的手上接上电极,这样就能测出手上的导电率。果不其然,摸牌的手指部位导电率最高。这个试验表明:通过身体生成的无意识感觉会先于有意识的决定。有趣的是,惠特曼有一首诗就叫《我歌唱带电的身体》。诗中写到:“身体是带电的,我们的神经伴随着微量电压的起伏在歌唱。”——他怎么知道的?
普鲁斯特都30多岁了还一事无成。因为得了哮喘病,他只能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他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写得令人望而生畏地冗长。出版商刚接到书稿,几乎绝望地问: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花30多页,写他翻来覆去在床上睡不着觉?书中最有名的一个桥段写到,普鲁斯特喝茶的时候尝了一口叫“玛德琳 ” (madeleine)的小点心。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浓茶碰到了普鲁斯特的上颚,顿时让他感到超凡脱俗,风轻云淡,就是这一点点小小的糕点,唤醒了他对童年的回忆,他想起了在贡布雷的时光:莱奥妮姑妈的老房子、乡间的路、花园里的花、河上漂浮的睡莲。普鲁斯特对记忆的观察细致入微,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出现“玛德琳效应”是因为味觉与嗅觉直接与海马体相连,而海马体是大脑长期记忆的中心。
普鲁斯特长久地沉浸在对回忆的玩味之中,他敏感地察觉,记忆并非是连续的,也不是录像机一般真实的复制。记忆中充满了错觉,比如他写到恋人艾伯丁:艾伯丁有一颗美人痣,但那颗痣到底长在哪里呢?一会儿,这颗痣长在下巴上,一会儿又到了唇边,最后到了眼睛下面的颧骨。普鲁斯特承认:越是回想,记忆就变得越来越不精确。神经科学的发展印证了普鲁斯特的猜想。我们总是喜欢把记忆想象成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实记忆不过是我们对过去的想象,很可能,我们对记忆的每一次想象都会和原有的事实离得更远。普鲁斯特是个改稿成癖的作家,他先是在手稿的旁边写上密密麻麻的注释,写不下就再找张纸连上,然后又把很多小便签贴在手稿的各处。我们的记忆也一样。一遍又一遍,我们都在修改着对往事的记忆,直到往事变成我们编织的故事。
195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声称,他发现了语言的深层结构。乔姆斯基的理论,和斯泰因小姐的文字游戏不谋而合。乔姆斯基讲到,人们一直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和后天习得的,但真实的语言结构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智深处。我们每个人,就像电脑一样,在出厂的时候就预装了一套语言体系。极端而言,所有的语言在结构上都是一样的,而与此同时,语言的边界又是无限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乔姆斯基的理论石破天惊,人们最初将信将疑。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在尼加拉瓜有一群失聪的孤儿,他们后来进了一所聋哑学校。所谓的学校,却没有什么老师。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学过语法,他们也听不到别人说话,但奇迹出现了,这些孩子之间开始打手势互相交流: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语言。低年级的孩子追随高年级的孩子,这套自我生成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巧。斯泰因小姐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用无穷的花样重复诉说着同样的事情。”如今,人们终于相信她的话了: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斯泰因小姐曾经感慨:以新的方式看问题真的很难。一切都突然成为阻碍——习惯、学校、日常生活、理智和懒惰。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天才真的很少。天才在于执着。塞尚坚信传统的绘画没有画出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眼睛并非构造精巧的照相机,如果你长久地注视一个事物,你可能会发现,左眼看到的和右眼看到的其实并不一样,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盲点。
人类的大脑再次欺骗了我们,通过后期加工,大脑使得我们相信,所见到的都是事实。塞尚晚年画的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色彩氤氲,迷蒙一片,但我们却仍然能够辨识出山水的秀姿。塞尚是对的,他画的才是我们真正看到的东西。人们原本以为他画的失真,后来才认识到,我们之所以不能接受他的创新,是因为他画的太过真实。斯特拉文斯基之所以故意引进不和谐音,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和弦才是音乐。音乐的感染力在于冲突,在于给我们带来困惑,如果我们只是接受“悦耳”的东西,那就只能越来越沉缅于怀旧金曲。斯特拉文斯基是对的。音乐是由大脑创造的,大脑几乎能够学会聆听任何东西。多年之后,《春之祭》成了好莱坞动画片的主题曲。
前卫艺术确实会令我们困惑,但若没有前卫艺术的晦涩,除了我们自己已知的东西之外,我们不会崇拜任何事物。
乔治·艾略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先锋文学家。她才华横溢,却为情所累。艾略特曾经和赫伯特·斯宾塞有过一段情缘,就是那位鼓吹“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家。她爱上了他,但他不爱她。斯宾塞坚定地回绝了艾略特的求爱。他的理由很简单:艾略特长得太丑了。但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却一眼看出艾略特的魅力。他写到:“起初,她真是丑极了,那是一种有趣的丑陋。而现在,在这奇丑无比之中却有一种最强大的美,并且,这种美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悄悄地把丑陋抹去,使你的精神被其深深吸引。于是,最后,你就会像我一样,深深地爱上她。”
无论是现代主义艺术,还是晚近的神经科学,揭示出的人类心灵奥秘都乍看起来混乱而又丑陋,和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但在这奇丑无比之中却有一种强大的美,于是,最后,我们都会深深地爱上她。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Jonah Lehrer, 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中译本为乔纳.莱勒,《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艺术与科学的交融》,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专辟了一章,写一位法国大厨对味觉的开拓性研究,喜欢法国餐的读者朋友不妨体会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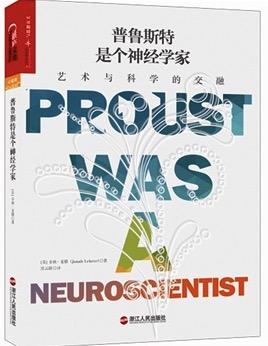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