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1.
见面之前,张平原校长并不知道我是谁。其实,见面之后,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他只是觉得有点好奇: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要跑到四川省广元市的山区去看他的学校:范家小学。
罗振宇的《时间的朋友》2018-2019跨年演讲开演之前,我告诉张校长:我的新书《变量》会在跨年演讲发布,而且罗胖会讲到范家小学的故事。
张校长说:哦,知道了。
其实,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罗胖是谁,也不知道跨年演讲是啥。他在心里纳闷:为什么新书要在半夜发布呢?人都睡了,发布给谁呢?他忍住没有问我。
2019年1月1日凌晨,张校长终于知道什么是跨年演讲了。罗胖在这场跨年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华彩乐章的部分,讲了范家小学的故事:一群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反而是最快乐、自信的孩子;一群像张校长这样的农村老师,正在努力地把劣势变成优势,让教育回归了本质。
这一夜,张校长根本睡不成觉。他的电话被打爆了。凌晨三点,还有记者要求采访。
天亮之后,广元市市长被惊动了。他问广元市教育局局长:发生了什么事?广元市教育局长打电话问张校长:何帆是谁?罗振宇又是谁?
正如张校长对跨年演讲一无所知一样,在去范家小学之前,我们也对农村学校一无所知。

2.
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范家小学的?
说来话长。
第一个线索是得到的CEO脱不花告诉我的。2018年春节之后一起吃饭,脱不花说,他们家曾经有个保姆,保姆的孩子在老家上初中,上的是个寄宿学校。保姆把手机里存的寄宿学校照片给脱不花看。虽然不如城里的私立国际学校那么奢侈,但这所农村寄宿学校的条件毫不含糊。当然了,价格也不含糊。一年学费三万。
脱不花问:你打工挣钱这么辛苦,怎么舍得送孩子去这么贵的学校呢?
保姆说:北京往外赶人,我们的工资行情就跟着涨。一个月涨了3000块,一年就是3万多,正好给娃交学费。
我听得哈哈大笑:聪明。
这个故事触动了我。我隐约觉得,我们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农村教育。

3.
我问脱不花:你们家这个保姆是哪里人?怎么找到这个学校?
脱不花说:她可能是四川人。不对,可能是湖北人。要不就是贵州人。
她一下子把我扔进了一片大海。
怎么才能从大海里捞针呢?我几乎动用了我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
我找到在四川教育厅挂职的一位朋友,但他已经结束挂职,回到上海了。他给我介绍了四川教育厅的几位同事,但他们对我说的这种农村学校茫然不知。我们拜访了来北京开会的甘肃省社科院专门研究农村教育的专家,但他们说,甘肃有的都是特别穷的农村学校,像你们说的这种学校,还真的没有。我们请教东北师范大学研究农村教育的学者,他们说,就算有这样的寄宿学校,父母不在身边,仍然解决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找到自己的母校,河南省实验中学,请母校的老师帮我找找河南的农村学校,也没有找到。
我几乎要放弃希望了。
有一次坐飞机。邻座的先生看了我一眼:你是何帆老师?我听过你的课。于是,我把手上的书放下来,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无意中说起自己在贵州有项目。我冒冒失失地问他:你熟悉不熟悉贵州的农村学校?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巧的很,他也想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记得有个人跟他说过这事,说是这人过去做包工头,后来生意难做,到贵州办民办学校。很像脱不花说的那种。寄宿学校,一年收费2万。2000学生,一年收4000万。支出大约2000万,这还是把老师的工资开得比公立学校老师更高。一年能赚2000万。社会地位也大不一样。当包工头的时候被人叫奸商,现在成了教育家。据说想进他的学校,得有市长的批条。
这位朋友问我:何老师,你觉得这样的项目值得投资吗?
柳暗花明啊。大约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开始上路。
我和我的团队去了贵州、福建、山东、广东,看了不同的农村学校。怎么说呢?失望居多。比如我们在贵州确实看到很多民办学校,但这不是包工头办的,大多是原来的公立学校老师辞职创办的,虽然办的也不错,挺赚钱的,但是,我看到的还是大班授课、军事化管理。有些农村学校会声称他们有创新,但我去看了,所谓的创新就是国学教育,比如背三字经。不过,这些调研也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猜想: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不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的目标,他们开始重视孩子生活能力、社交能力的培养。我看到的农村学校,跟我小时候上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土墙、黄土操场、室外的“礼堂”,农村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4.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故事。
真正的转机是我们联系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他们告诉我,你们想找到的学校我们知道哪里有。我们把这些学校叫做小而美学校。我们刚刚评出五个小而美种子学校,想不想来看看?
当然想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其中有一家小而美种子学校就在北京。这是北京房山区的蒲洼小学,大致就在著名的京郊景点十渡。
6月4日,我一大早打车从市里去房山。进山之后,漫长的山路,好像没有尽头。我盯着手机GPS导航。快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跟司机说,等等,我下去买瓶水。我担心万一山区里连自来水都没有,一天下来不得渴死了。
事实证明,我太自作聪明了。我看到的蒲洼小学,硬件比在市内的老牌公立学校还要好。学校老师有硕士毕业的,工资比市区的老师还高。操场上汇报演出,居然有四块液晶大显示屏、拍电影用的摇臂、摄影师恨不得比嘉宾还多。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穿白衬衣黑裤子,胸口别着党徽。学生统一校服,干净整齐。
我们还见到了一批推动农村教育的志同道合者,比如曾任北大附中校长的康健老师。这次调研还是没有说服我,蒲洼小学有很多有意思的创新,这些孩子也确实是留守儿童,他们见到老师们都落落大方,有说有笑,不过,我看到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还是很拘谨,汇报他们项目的时候居然提到了荣格----这不小心暴露出来,其实是老师帮他们写的台词。虽然美中仍有不足,但我从蒲洼小学出来,就知道这个选题有戏了。
我想找的那个学校一定存在。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儿。

张校长和何老师看孩子们玩滚筒游戏
5.
我的研究助理许多多兴奋地告诉我:何老师,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她们按照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线索,一家一家拜访,来到了四川广元。广元有两个“小而美”种子学校。她们先去看了一所,条件更好,但还是没有感觉。许多多一边在微信群里给我发“现场报道”,一边抱怨:为什么孩子们一上台就自动变成了朗诵腔呢?第二天,她们到了范家小学。许多多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范家小学不一样,何老师,你一定要来看看。
当时,我的行程表上还有:去新疆看极飞的无人机、到北戴河看阿那亚社群重建、到欧洲开会讨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我本来想早点去范家小学,张校长告诉我的助理,让何老师晚些时候再来吧,现在山里发洪水,还在修路,他来了也进不了山。这一等就到了九月初,我们特地选了开学的时候过去。
我在范家小学前后待了五天,跟老师们聊天,跟孩子们玩耍,到村里跟村民摆龙门阵,到学生的家里去家访,跟校长一起爬山,带着孩子们在河边打水漂。
我跟张校长说,能不能请几个孩子带我去村里转转,看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乡村调查的。范家小学曾经让孩子们去找村里的一口老井。这口老井一般的村民都不知道在哪儿,只有几个老人还能找得到。当年,有个知青跳井自杀,村里觉得不吉利,就把水井给填了。当然,孩子们的发现是,现在都用自来水了,不需要水井了。
罗胖跨年演讲讲到范家小学,给观众看的几张照片,就是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找那口水井时拍的。
回到学校,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三个小姑娘带我去村里,整个班的课程都要调整。这个班一共六个学生,我一下子带走了一半。

6.
有个记者很不服气。她说,我自己在农村支教了几个月,你只待了几天。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能看到真相呢?
如果你在三天之内还看不到真相,那么,三个月之后你仍然看不到真相。
当然,三个月之后你会看到更多的真相。在范家小学的那几天,我也不是没有发现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最大的担心是,范家小学当然能够把孩子培养得阳光自信,但他们要是到了别的学校读中学,“孩子社群”变了,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仍然乐观积极呢?
我也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小学建好,就不可能重建农村的社群。
我也感受到了张校长的焦虑:他担心农村小学留不住老师。情怀不能当饭吃啊。
我也看到很多读者的留言,他们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孩子放弃高考,真的是件好事吗?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你怎么会觉得农村孩子的人生道路更宽阔了呢?父母不陪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没有负面影响?你说的那些教育创新,难道城里的名校、国际学校做不到?
谢谢你们的问题。我会在我的得到课程《何帆报告》里做个加餐,专门回答这些问题。

7.
但是,这篇文章讲的不是教育,只是花絮。
这篇文章告诉你,在罗胖跨年演讲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背后,是我们团队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跑了六个省,采访了将近上百位专家、老师、家长、孩子,四面出击、八方求助,不断修正自己的预设框架,不断颠覆自己原有的认知,不断打磨自己的叙事模式,最终为你找到的一颗珍珠、一股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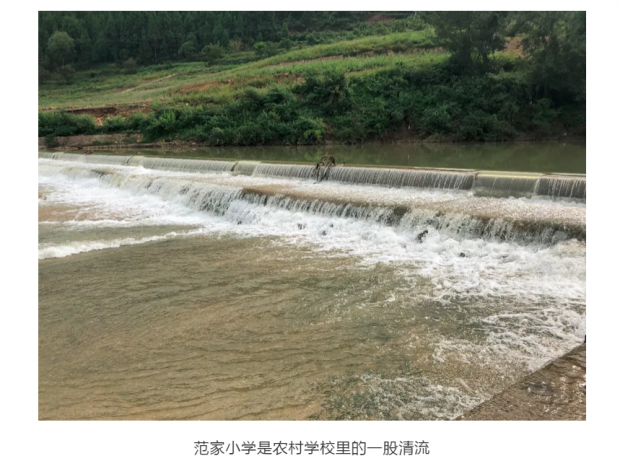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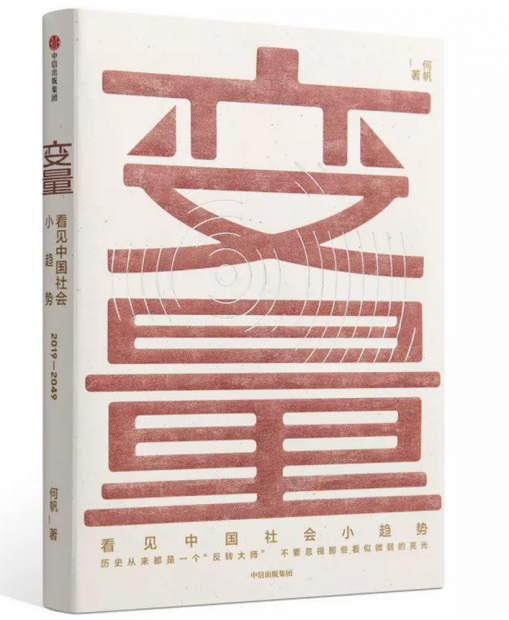
点击此处购书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