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很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在中国强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非常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地方政府官员最热衷的事情是招商引资、修路建厂。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
钱颖一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借助管理学的思路,分析了U型组织和M型组织的区别,强调中国始终无法实现经济集权,中国的小企业众多、工业化程度不高,各地情况差异极大,所以不得不接受分权的现实,而分权恰恰有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张五常教授也指出,县域的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张军、周业安等学者也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锦标比赛”做了深入的分析。傅勇博士是国内最早提出“中国式分权”的学者之一。和别的学者不同,他有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丰富经验,对中国经济现实有敏锐的观察。他在已有的学界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金融分权”的概念,并以此为主要线索,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宏观失衡。
所谓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分权并非把权力一分了之。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但仍然保留着对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控制,也会不断地对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边界进行调整,时放时收,相机抉择。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两个鲜明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投资基础设施、重化工业和房地产,同时采取了各种对投资者亲善的优惠政策。很多能干的地方官员,看起来更像是企业家,而非行政官僚。如果哪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证明当地官员的执政能力更强,他们也就有更大的晋升机会。当然,也不必讳言,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项目投资,是有不可告人的“寻租”动机。
二是中国经济的波动性很强,总是大起大落。这和“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放权-集权周期是有关的。政府鼓励下的经济增长经常会比由市场经济力量自发推动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但也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旦出现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就会采取各种紧缩手段。不仅在货币政策上抽紧银根,还要在产业政策上压缩产能,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责权边界。这种频繁的调整加剧了经济波动。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本来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但在中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反而扩大了波幅。
在研究“中国式分权”的时候,学者们大多更注重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也就是说,对“财政分权”关注得更多。有些学者试图从财政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正如傅勇博士指出的,增长动力是制度化的,经济周期却起起落落。经济周期有长有短。长周期更多地受到重大技术变革的影响,短周期则更多地受到货币、信贷因素的影响。傅勇博士提出,金融分权是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的更重要的原因。
这一判断是基于一个事实,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控制主要依赖金融调控,而非财政制度。围绕着中央-地方关系的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总的方向是趋于更加规范和稳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收放主要体现在货币、信贷政策方面。就以著名的四万亿刺激政策而言,尽管看起来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正如我们随后看到的,真正起作用的是2009年出现的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的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并用于热火朝天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也广泛参与了多层次的金融资本市场。除了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还有各地的城商行、乡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政府在支持本地企业上市的时候也非常积极。各地的产业投资基金、各地兴建的各种类型的交易平台层出不穷。
“金融分权”才是房间里的大象。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文献一直忽视了这一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受市场供需决定的,不可能出现地方性的分割市场。但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依然模糊。更为复杂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半政府、半市场的,这是“金融分权”的重要制度背景。
傅勇博士认为,自建国以来,金融集权-分权的体制演变经历了五个周期: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金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就连中国人民银行,也一度被撤并,和财政部合署办公。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独立。由于实行“条块结合”的信贷管理模式,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均由总行和地方政府双重管理,地方政府获得了广泛干预金融资源分配的权力。这导致了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后,金融权力开始由放到收。第三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8年,总的趋势是中央收回地方的金融资源分配权。这不仅是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更多地是出于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第四阶段是2008年到2012年。由于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加大资金配套力度,允许地方通过融资平台扩大向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举债。这是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大爆炸”。其好处是迅速拉动了中国经济复苏,但弊端是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第五个阶段是从2013年开始的,这一阶段的主要方向是如何跳出集权-分权周期,打破治乱循环。
傅勇博士建议,一个重要的改革应该是大力推进市政债,把过去的“土地财政+平台融资”模式改变为“财产税+市政债”模式。由于地方的税收收入不足以支撑其支出,所以不得不依靠卖地的收入。“土地财政”带来的恶果是房地产业绑架了地方政府,地价和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降,而且,这是一种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红利的急功急利的做法。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向银行借款,可能加剧“期限错配”:地方投资的项目都是长期的,但银行贷款却大多是短期的。同时,这些贷款很难追溯,很难做到透明化和政务公开。如果通过引进财产税等地方税种,增加地方的税收收入,同时推动市政债的发行,可以从制度基础上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傅勇博士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近约束”。企业可能面临“硬约束”或“软约束”。如果企业面临“硬约束”,挣到钱才能生存,赔了钱就要破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克勤克俭、锐意进取。如果企业面临“软约束”,赔了钱还有政府补贴,自然会滋生懈怠散漫的情绪。同样,如果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面临的是“远约束”,自主性很可能会降低,“跑部进京”现象会更严重,资源会出现更多错配。发行市政债,用“近水”来解近渴,再进一步吸引“远水”来解“近渴”,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要发行市政债,必须说清楚项目的目的、偿债来源、资金使用情况,这就使得融资更加阳光化,有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大众实施监督功能。其功效不仅仅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降低金融风险方面,从长远来看,提高治理能力、培育民主政治,亦依赖于公共财政的实践。
点评完傅勇博士的主要观点,我想再谈一下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两点个人心得。
一、为发表的研究和为兴趣的研究。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在过去二、三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后起之秀的理论功底更为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广阔。遗憾的是,在年轻学者中,为发表而做的研究多于为兴趣而做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在高校系统,而要想在高校晋升,就必须要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最近的学术考核更加注重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但国际学术期刊并不是特别关心中国经济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很多青年学者不得不暂时压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转而为发表而做研究,什么题目更容易发表就研究什么。傅勇博士是一位难得的政府体制内的学者,他做学术研究,并非是为了功利,更多地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对中国经济的关切,以及一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这可能恰恰是他能够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的原因。
二、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有些学者喜欢自称是做理论研究的,不关心应用研究。在经济学这种与现实问题高度结合的社会学科中,所谓的纯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当一个学者说他是做理论研究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清晰而有趣的问题。在学术界看来,似乎政策研究是不入流的,但我认为,恰恰是政策研究才能催生经济学的变革,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领域。坦率地讲,我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知之甚少,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负利率,收入不平等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我们都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有先提出好的问题,才能引导有意义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傅勇博士的研究,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路标”,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推动经济学出现真正的革命。
注:本文为作者为傅勇新书《中国的金融分权与经济波动》写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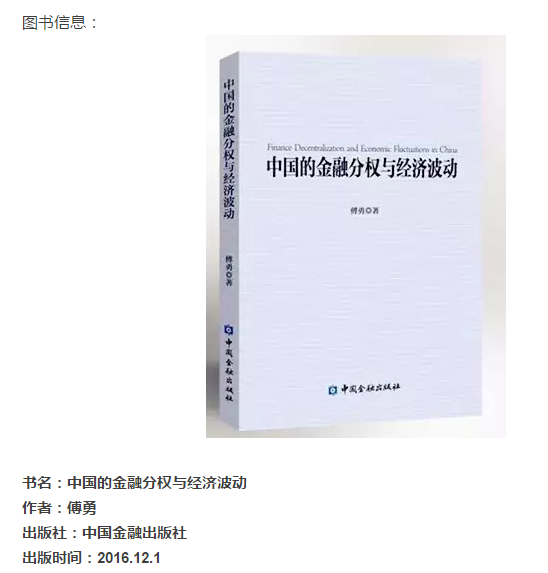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